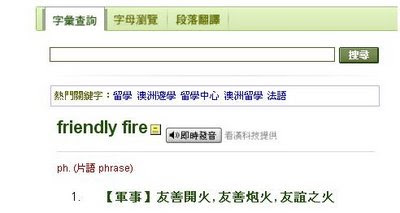續
前文,原文為
Not So Dire Straits ;How the Finlandization of Taiwan Benefits U.S. Security
刊載於《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一月二月號
芬蘭化直接挑戰了主流現實主義派的對於冷戰的思維邏輯。因芬蘭對於蘇聯強權的讓步並不能滿足莫斯科亟欲擴張的胃口。即使有人反對芬蘭化理論,但也很難否定掉前芬蘭總統佳勒貢在冷戰結束時期有著積極的貢獻。舉例而言,在1969年,芬蘭做為兩大集團的開會地點並且簽署了一份對於人權及自由達成共識的文件:《赫爾辛基協議》〈the Helsinki accords〉
冷戰歷史學家,如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認為赫爾辛基進程對於削弱蘇聯的道德權威上十分關鍵,而許多學者則辯稱此舉在1980年代中葉啟發了戈巴契夫的意識形態轉變。此外,芬蘭與莫斯科間特殊的對話關係也使得莫斯科第一次裁減核子武器談判、北極天然資源開發協商得以成行。這兩次會議對於增進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與蘇聯集團的關係而言是個成功的樣板。儘管「芬蘭化」通常帶著負面的意涵,但卻不必完全是貶抑之詞。
台灣與1940年代晚期的芬蘭有些許特徵類似。面積很小但是在國內擁有主權,與鄰國的超級強權有著文化與歷史上的聯繫。強烈的獨立意圖需要遷就於強權國家重要利益。更重要的是,這兩個國家的人民與領袖將眼光放在集體的安全而不是提升衝突。此舉可以幫助我們在全球政治中解決最需要擔憂的趨向:不斷升高的中美競爭與對抗。
但這個類比並非完美無懈可擊的。儘管有些人會質疑北約會站在芬蘭一方抵擋蘇聯的侵略,但美國今日所保障台灣的安全,相較冷戰時期保衛芬蘭而言十分明確。而中國為數1000枚、甚至數量更多瞄準台灣的導彈,比起蘇聯曾駐紮在武克希河〈Vuoksi River〉畔的軍隊是再直接而不過的威脅。但大致而言,中台兩方相同的想法促成的第二次低盪和解可以比擬為芬蘭與蘇聯在冷戰期間的低盪和解。雖然言之過早,但是台北政府正無可避免的朝向芬蘭化的方向。
在這套劇本中,台灣大概會重新定為中立性的角色,而不是成為美國的戰略夥伴。藉此減輕北京政府的疑慮,懼怕台灣將成為中國區域性軍事與商業發展的阻礙。一旦台灣成為中立性的角色,也不再成為削弱中國共產黨統治的桎梏。而回報的是北京去除武力威脅,允許台灣參與國際性組織,並且給與這個島更多有利的經濟與社會福利。
民進黨國際事務部主管蕭美琴,形容在台灣的對中國政策改變為“取代以往與美國假設性的非正式同盟關係,正以一個戰略性的前景,與中國的影響力同進。”儘管蕭美琴與其他民進黨黨員一樣害怕改變,但對這樣的改變採取保留的態度並非無所根據。
手法亦或是結果?
檢視中國對於台灣政策的轉變有兩種看法。普遍的看法認為北京長久以來為民族主義所使,而中華人民共和國聲稱要收復台灣的想法則是明顯的來自於國恥,與國家的短處被揭發。根據這個論點,中國共產黨亟欲逼迫台灣就範〈reincorporate〉,以避開國內民族主義的反撲與被質疑統治權正當性的危機。從這個觀點出發,台灣是個被併吞的結果,第二次低盪和解只不過是個迂迴地以武逼統的手戰略性改變:在北京的絲製低盪手套下藏著民族主義的鐵拳。
近幾年來,許多西方的分析家放棄使用民族主義的角度詮釋對於台灣的政策,並且傾向使用地緣戰略的角度解釋。失去而不可復得的領土在中華人民共合國上多的是,中國對於那些領土毫不眷戀〈包括與蘇俄、印度邊境地區還有在蒙古與韓國控制下的幾個小島〉。然而台灣在地理上優渥的地位,代表了對於中國潛在性的戰略威脅。它可以成為外國軍事部隊進犯中國的基地,即使在承平時期,也可以限制北京研發投射海軍武力,並確保外國勢力在東亞的航行的安全。
由此觀之,北京的核心目標在於台灣其快捷的離島優越性,尤其在2009年,當五艘中國船隻跟蹤一艘航行於中國潛艇基地附近的美國海軍船隻此事件即可映證。如果台灣不足以自我防禦、具有中立國的地位,沒有與中國大陸有緊密的政經關係,則台灣代表的是配滿了先進美國武器的美軍戰略性同盟。北京經常改變對台灣的定位。從毛澤東的時代開始向中間理性路線修正,從“解放”到“和平統一”,從“一個中國”到“反對台獨”,這顯示出了台灣戰略地位現狀的重視,而並非其對中國明確的政治關係。這個解釋說明了北京政府無意佔據或統治台灣;而是想要在世界強權中增加影響力,而同時希望台灣是個中立的國家,而不是代理權政府。用這個看法來解釋,台灣的芬蘭化並非是一個結局而是種手段,第二次低盪和解是個達到這個戰略性目標的一種手法。
中國最近的表現證實了這個看法;北京允許台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WHO〉的決定,冷靜地理解了讓台灣在國際上更多發聲的機會,並讓台灣更不依賴美國。而這好符合中國己身的國家利益。此舉也給北京一個機會展現出中國掌控下的亞洲也可以維持和平、繁榮甚至民主。威斯康辛大學史提芬角分校的中國籍教授王建偉〈音譯,Jianwei Wang〉也提出他的看法:「北京政府視處理台灣問題及海峽兩岸關係為和平崛起、置身國際事務中不可或缺的一個環節,而不是單純的影響國家榮耀的單一議題而已。」
最近一份調查資料顯示了這個爭議的可信度。在2004年, Horizon 研究機構針對中國大陸國民的民調顯示大陸並不特別用民族主義收復台灣。只有一成五的人想要立即採取軍事行動,而五成八的人認為政府應該揚棄使用武力而以經濟整合取而代之。在2008年的一場演講中,胡錦濤定位兩岸關係所面臨的問題在於敵對狀態而非政治上的分離,並且推翻了先前北京的看法。隨後中國共產黨的政策聲明也揭露了對台灣地緣戰略上,而並非誇張的民族主義急統。
綏靖主義者
1995年,第一次低盪和解結束。台灣學者,同時也是國民黨的顧問嚴震生,在台灣政治期刊《問題與研究》上詳盡的敘述了台灣芬蘭化的邏輯。藉著北京的同意尋求更多國際的聲音,保持不要威脅中國的外交政策,並且選擇讓北京信任的領導人。嚴震生辯駁,如果不要在中國的門戶上挑戰正在這個崛起中的超級強權,台灣可以在保護內部自治與經濟繁榮上達成更多。此外,長遠來看,只有在中國的民主化後,台灣才有可能得到真實的獨立,而台灣應該儘量避免挑起軍事與意識形態上的衝突。嚴震生引用雅典人修昔的底斯的著作《米洛斯人的對話錄》“既被賦予保護國家未來存續的重責”嚴震生說,“一個文明的國家應該考量內部現實並自我調適策略”。十年後嚴震生的前衛觀點才成為顯學,而今天已經得到廣泛的支持。
馬英九從他上任以來,追求“關係正常化”已經贏取了台灣人廣泛的支持。所反映出的是自蔣毛時期,台美的戰略思維,認定使用的武力手段解決台海問題,已不符合今日台灣的需求。如同芬蘭,一個小小的國家,卻是使用非武力手段解決冷戰的先驅。台灣在亞洲即將發生的美中冷戰關係中也可以扮演芬蘭的角色。
今天的中國成為世界的威脅是因為中國內部的政治並不開明,沒有良法節制中國的經濟與軍事力量。台灣芬蘭化的角色將遠助於幫助中國的自由化,而官員也能夠比現在更能跨越海峽。重量級的中國自由派,如中國社科院的張寶樹,認為中國大陸應該汲取台灣政治發展的經驗。國立新加坡大學的博士盛立軍也這樣寫道:“隨著台灣的政權遞嬗,北京遲早會得要改善其治理之道〈包括民主、人權與反貪腐〉”台北的民主經驗提供了北京許多寶貴的經驗,特別是先前是獨裁的國民黨在2008年重回執政,顯示出即使中國民主化,另外一個黨上台後,中國共產黨仍有可能會再次執政。
趕上台灣的想法,會對中國自由改革推波助瀾〈中國人已熱切吸收台灣的流行文化與生意模式〉在某些層面來說,處理兩岸關係非理性的一面,也符合台灣選民對透明度與可靠性的期待。有些人稱之為綏靖主義,但如果台灣使用綏靖主義合緩中國、使崛起的中國民主化,也值得一試。
推銷芬蘭化
台灣的持續朝向芬蘭化與否,端視馬英九是否能夠向台灣人民展現出這個政策的具體成效。馬英九應獲取國際上更多贊同台灣的聲音〈舉例而言,得到永久的世衛觀察員法理地位〉、能獨立交涉免稅協定,並且確保能移除瞄準台灣的一千多枚導彈。最好能夠與中國達成和平協議,除非台灣被侵略或是法理上台獨,讓中國放棄使用武力解決台灣問題。如果達成以上的協定,就如同1948年蘇聯芬蘭條約一樣,緩和了大國國家安全上的顧慮,而確保了小國的自治。另外一個潛在的好處是台灣將與北京政府簽訂免稅的經濟合作架構協定。台灣目前在中國市場面臨危機,且在中國供應鏈中缺乏競爭,乃因為東協與中國的免稅協議。
馬英九同時也要向台灣的選民保證他們不會失去政治上的自由。在台灣,有足夠的理由與看法認為掉入中國整合的陷阱中將會損害台灣的民主與內部主權。〈同時,北京害怕隨著台灣參加國際性組織增多,會擴張台灣外部的主權〉威士康辛大學研究中國人民共產黨戰略觀點的王先生,預言馬英九最終會理解到統一是長期目標的選項,並且會縮小台灣軍購的規模。王先生在解讀芬蘭化對於台灣而言需要付出代價這點上正確。特別是在類比芬蘭這點上,台北政府需要在島上約束反對共黨的抗議活動,並且與美國軍方保持距離。
〈待續〉